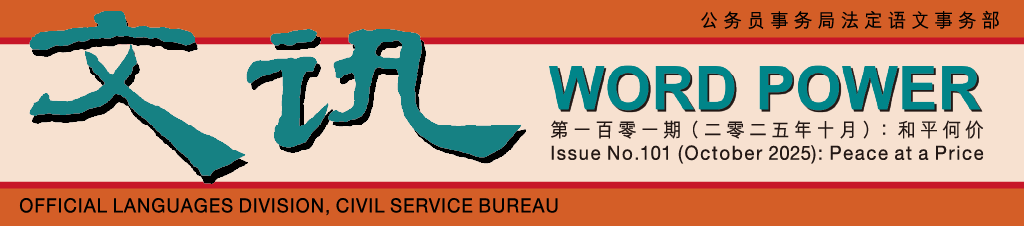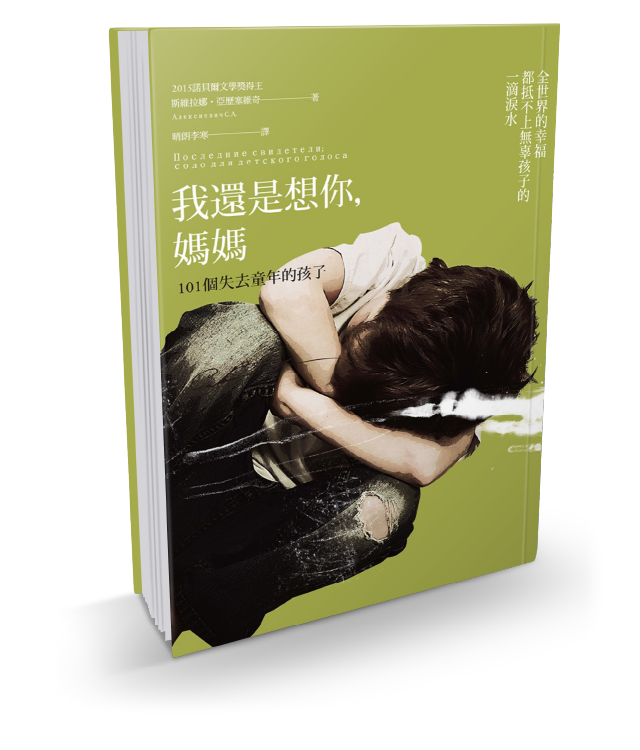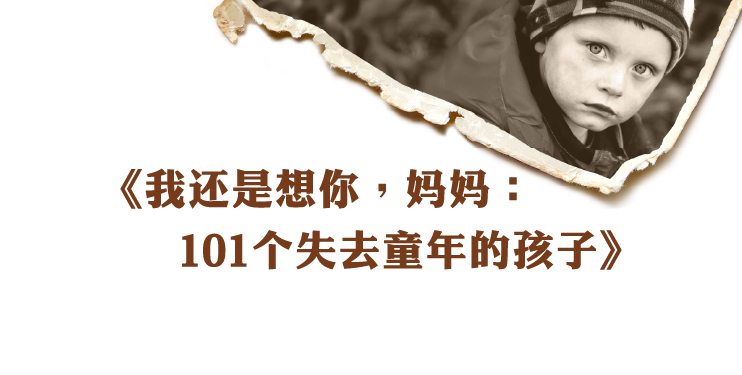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一年夏,苏联遭纳粹德军入侵,数千万人伤亡,当中包括数百万儿童。战后出生的白俄罗斯作家亚历塞维奇(Svetlana Alexievich)回首这段烽火岁月,借平民百姓之口述说历史。她走访苏联各地,花上数年时间搜集资料,写成《我还是想你,妈妈:101个失去童年的孩子》(Last Witnesses: Unchildlike Stories)。这部口述纪实文学作品在一九八五年出版,记述一百零一名受访者的战时回忆。
这些人物儿时经历雷同,正好互相佐证,说明个人的悲剧其实是一整代儿童的集体回忆。小故事就像一片一片拼图,拼凑成一个时代的写照。
小孩对战祸和死亡没有概念。看见敌机在空中盘旋,只觉精彩,高声欢呼,不知道危险。看见村子着火,以为是漂亮的篝火,不会想到有人家园尽毁。四岁小孩呆呆地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,不明白她怎么会死。十一岁的爱德华陪邻居上街寻父,翻转满街躺着的死人,不当一回事。
纵使战争结束,活下来的人也未必得到真正的安宁。十二岁的阿尼娅从列宁格勒被围开始经历饥荒,那时大伙儿吃光了公园和植物园的植物,甚至要吃泥土。十多年过后,她才能走出阴影,感受到纯粹来自鲜花嫩草的快乐。四十多年后,她在电视上看到饥民空洞的眼神,仍无法承受,情绪失控。战争创伤挥之不去,遗憾无从弥补。另一个叫季娜的受访者已为人母,说到四十多年前空袭时失散的至亲,依然无法释怀:“我还是想念妈妈。”
十岁的萨沙家园被毁,一家人投靠游击队。队员跟他聊天,问他想在路旁松树下找到糖果、饼干还是麫包。萨沙的答案竟是子弹。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,对德军同样深恶痛绝。不过,也有些孩子跟敌人接触后,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前面所说的爱德华逃难路上遇到德军,要他帮忙照料伤兵。看着敌人全身打哆嗦的痛苦样子,爱德华心情复杂,多年后仍无法说得清楚:“厌恶?不是。仇恨?也不是。那是复杂的感觉。其中也夹杂着怜悯……人类的仇恨也需要形成过程,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。”
战争摧毁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。家园尽失,妻离子散,使人生活在绝望之中,但平凡人舍易取难的道德抉择,带来一点希望。不少苏联人历尽劫难,遇上德军战俘却非但没有报复,反而向弱者施以援手。战事平息后,吃遍公园植物的阿尼娅在孤儿院生活,某天午餐后遇上一个德国战俘。他嗅到食物的气味,就站在她旁边,嘴巴不由自主地在动,像是在咀嚼一样。阿尼娅心中不忍,把一小块余下的麫包送了给他。往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,院里的孩子都偷偷给这些战俘留食物。战争虽夺去快乐童年,却没有让他们变得狰狞可怕,失去人性最宝贵的同情心。
尤为温暖人心的是,没有被仇恨蒙蔽的,不止是心思单纯的孩子。瓦洛佳一家都加入游击队,哥哥不幸牺牲。有一次瓦洛佳母亲提着马铃薯,对讨食的德国战俘说:“不给你。说不定,就是你打死了我儿子。”她说罢就走开,但之后又折回掏出几个马铃薯给对方。瓦洛佳后来才明白,这是母亲给孩子爱的教育。孤儿瓦夏获部队收留成为下士,随军攻打德国。他看见好友维佳跟德国小孩玩游戏,还把军帽送了给对方,大怒之下,把维佳关起来。指挥官知道后把瓦夏叫来,谆谆善诱:“你们都是好孩子,不管是苏联或德国的孩子,谁都没有错,战争快结束了,你们要相互友好对待。”真正的和平,并非只是终止战斗,而是放下仇恨。
亚历塞维奇以文学手法重现受访者的口述内容,忠实记录隐伏其中的细微情感,掌握时代和历史的脉搏。她用孩子纯真明净的眼睛来看这段血泪史,将战火的残酷无情如实呈现。二零一五年,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正如评选机构所言:“其有如复调音乐般的作品,为当代世人的苦难与勇气树立了碑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