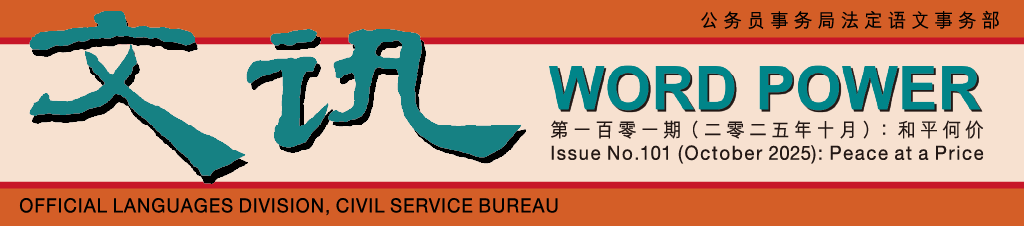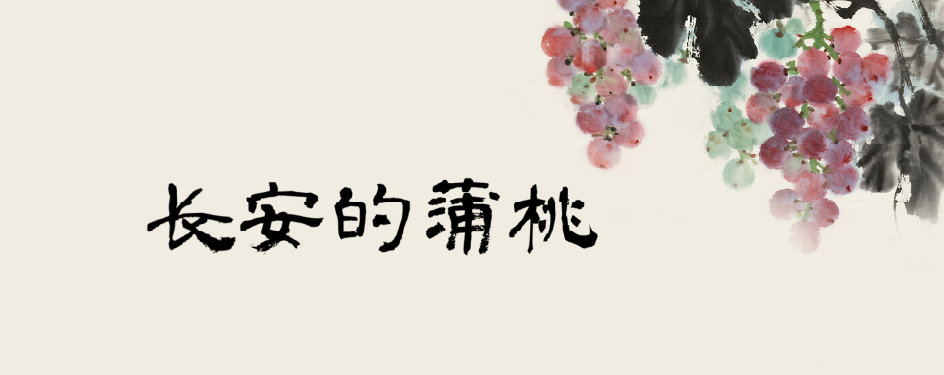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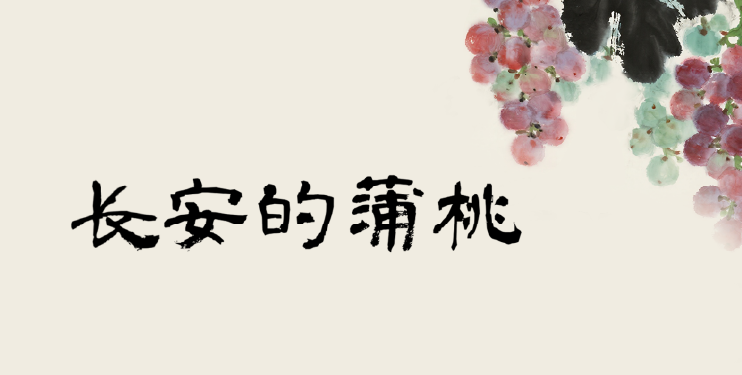
“强汉盛唐”,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两个朝代,也是开疆拓土的时代。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背后,却是流离失所,战火烽烟。诗人如何把眼前生灵涂炭的情景化为掷地有声的诗句?
汉乐府素以质朴自然著称,善用白描手法传递真挚动人的情感。“战城南,死郭北,野死不葬乌可食。”《战城南》首句直指战争的残酷:阵亡的士兵无人收殓,逃不过被乌鸦啄食的悲惨命运。战事频仍的结果不只是尸横遍野,更是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破坏:“梁筑室,何以南?何以北?禾黍不获君何食?愿为忠臣安可得?”桥上建造防御工事,南北无法往来,道路不通,庄稼无人收割。食不果腹,要为国尽忠又谈何容易。
残酷的不单是战事本身,还有因为长期征戍引致骨肉分离,老无所依。描写老兵退役归家的《十五从军征》,读来令人心酸。老人家“十五从军征,八十始得归”,当兵六十余年,归来已是家破人亡。昔日居处松柏成荫,坟冢累累。“兔从狗窦入,雉从梁上飞”,庭园荒芜,杳无人烟,老兵煮好饭菜亦无人分享。“出门东向望,泪落沾我衣。”戎马一生,只落得晚景凄凉。
自初唐灭东突厥到晚唐黄巢之乱,两百多年大唐烽烟不断。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,更令金玉其外的大唐露出其中败絮。王昌龄《塞下曲》的“黄尘足今古,白骨乱蓬蒿”,杜甫《兵车行》的“君不见,青海头,古来白骨无人收”,都直指乱世中人命如草芥。暴于荒野的白骨,一去不返的征夫,都是战事连年的铁证。
杜甫另一首名作《垂老别》写于安史之乱,以正要踏上征途的老翁之口,道出战争如何惨烈。“积尸草木腥,流血川原丹”,草木散发尸臭,平原山川被鲜血染红,触目惊心。白居易《新丰折臂翁》的主人翁用大石捶断手臂,以自残避过远征南诏,“一肢虽废一身全”,算是如愿以偿,但旧患缠身数十载,每逢风雨阴寒,便痛得无法成眠。他却说:“痛不眠,终不悔,且喜老身今独在。”这种喜是何等悲酸讽刺。
唐代诗人喜欢以汉朝比拟本朝,原因有二:一是大唐之前只有大汉能与之媲美。二是要批评当朝国事,只能委婉其词,借古讽今。反对长年征战、同情戍兵征夫的诗人,自然把汉朝的人物和典故写进诗中,以汉代唐,发出不平之鸣。
“誓扫匈奴不顾身,五千貂锦丧胡尘”出自陈陶的《陇西行》。匈奴与汉朝交战百余年,到唐朝时已与中原民族融合,史册再无“匈奴”之名。奋不顾身的汉家兵将,其实是大唐男儿。杜甫《兵车行》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”一句,谓汉武帝出兵开拓边疆,大批士卒阵亡,仍无止息之意,其实是批评唐玄宗好大喜功,为开边而频繁征兵。
李颀的《古从军行》同样以汉家借代李唐,不同之处在于加入意味深长的典故。“闻道玉门犹被遮,应将性命逐轻车。年年战骨埋荒外,空见蒲桃入汉家。”这段历史与汗血宝马引发的战争有关。汉军西征大宛,因断粮而无法攻克,将军上书请准罢兵。汉武帝龙颜震怒,遣派使者挡住玉门关,不准撤退。士卒后无退路,只能继续作战。虽然汉宛之战以大宛投降告终,但天下虚耗,数万兵卒葬身异乡,对大汉并无实益,只是让长安的皇亲贵胄能啖尝西域的葡萄罢了。
诗人把征夫戍卒的血泪凝炼成诗,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仍能看到硝烟不绝的战场,听见黎民百姓的悲歌,更加明白和平可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