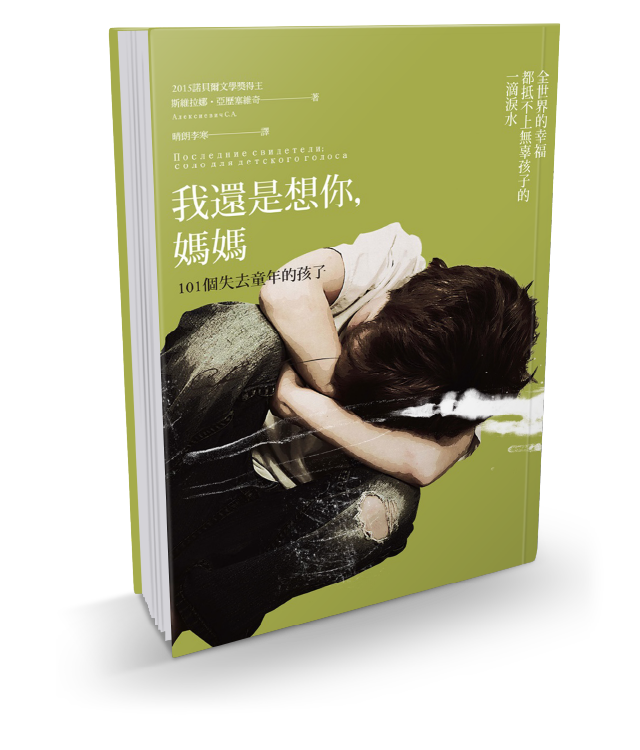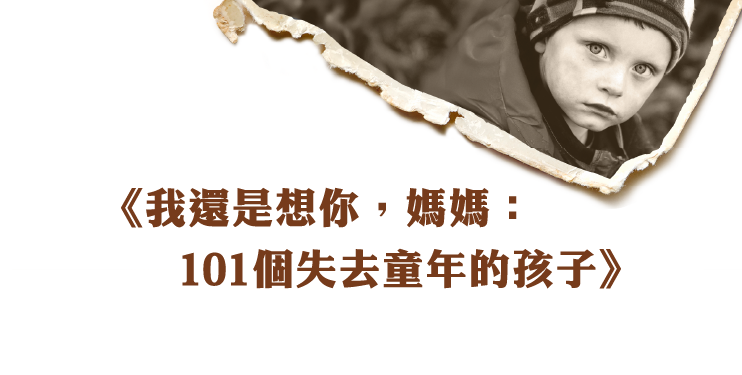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一年夏,蘇聯遭納粹德軍入侵,數千萬人傷亡,當中包括數百萬兒童。戰後出生的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(Svetlana Alexievich)回首這段烽火歲月,借平民百姓之口述說歷史。她走訪蘇聯各地,花上數年時間蒐集資料,寫成《我還是想你,媽媽: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》(Last Witnesses: Unchildlike Stories)。這部口述紀實文學作品在一九八五年出版,記述一百零一名受訪者的戰時回憶。
這些人物兒時經歷雷同,正好互相佐證,說明個人的悲劇其實是一整代兒童的集體回憶。小故事就像一片一片拼圖,拼湊成一個時代的寫照。
小孩對戰禍和死亡沒有概念。看見敵機在空中盤旋,只覺精彩,高聲歡呼,不知道危險。看見村子着火,以為是漂亮的篝火,不會想到有人家園盡毀。四歲小孩呆呆地看着牀上奄奄一息的母親,不明白她怎麼會死。十一歲的愛德華陪鄰居上街尋父,翻轉滿街躺着的死人,不當一回事。
縱使戰爭結束,活下來的人也未必得到真正的安寧。十二歲的阿尼婭從列寧格勒被圍開始經歷饑荒,那時大伙兒吃光了公園和植物園的植物,甚至要吃泥土。十多年過後,她才能走出陰影,感受到純粹來自鮮花嫩草的快樂。四十多年後,她在電視上看到饑民空洞的眼神,仍無法承受,情緒失控。戰爭創傷揮之不去,遺憾無從彌補。另一個叫季娜的受訪者已為人母,說到四十多年前空襲時失散的至親,依然無法釋懷:“我還是想念媽媽。”
十歲的薩沙家園被毀,一家人投靠游擊隊。隊員跟他聊天,問他想在路旁松樹下找到糖果、餅乾還是麫包。薩沙的答案竟是子彈。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,對德軍同樣深惡痛絕。不過,也有些孩子跟敵人接觸後,有不一樣的感受。前面所說的愛德華逃難路上遇到德軍,要他幫忙照料傷兵。看着敵人全身打哆嗦的痛苦樣子,愛德華心情複雜,多年後仍無法說得清楚:“厭惡?不是。仇恨?也不是。那是複雜的感覺。其中也夾雜着憐憫……人類的仇恨也需要形成過程,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。”
戰爭摧毀千千萬萬家庭的幸福。家園盡失,妻離子散,使人生活在絕望之中,但平凡人捨易取難的道德抉擇,帶來一點希望。不少蘇聯人歷盡劫難,遇上德軍戰俘卻非但沒有報復,反而向弱者施以援手。戰事平息後,吃遍公園植物的阿尼婭在孤兒院生活,某天午餐後遇上一個德國戰俘。他嗅到食物的氣味,就站在她旁邊,嘴巴不由自主地在動,像是在咀嚼一樣。阿尼婭心中不忍,把一小塊餘下的麫包送了給他。往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,院裏的孩子都偷偷給這些戰俘留食物。戰爭雖奪去快樂童年,卻沒有讓他們變得猙獰可怕,失去人性最寶貴的同情心。
尤為溫暖人心的是,沒有被仇恨蒙蔽的,不止是心思單純的孩子。瓦洛佳一家都加入游擊隊,哥哥不幸犧牲。有一次瓦洛佳母親提着馬鈴薯,對討食的德國戰俘說:“不給你。說不定,就是你打死了我兒子。”她說罷就走開,但之後又折回掏出幾個馬鈴薯給對方。瓦洛佳後來才明白,這是母親給孩子愛的教育。孤兒瓦夏獲部隊收留成為下士,隨軍攻打德國。他看見好友維佳跟德國小孩玩遊戲,還把軍帽送了給對方,大怒之下,把維佳關起來。指揮官知道後把瓦夏叫來,諄諄善誘:“你們都是好孩子,不管是蘇聯或德國的孩子,誰都沒有錯,戰爭快結束了,你們要相互友好對待。”真正的和平,並非只是終止戰鬥,而是放下仇恨。
亞歷塞維奇以文學手法重現受訪者的口述內容,忠實記錄隱伏其中的細微情感,掌握時代和歷史的脈搏。她用孩子純真明淨的眼睛來看這段血淚史,將戰火的殘酷無情如實呈現。二零一五年,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。正如評選機構所言:“其有如複調音樂般的作品,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碑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