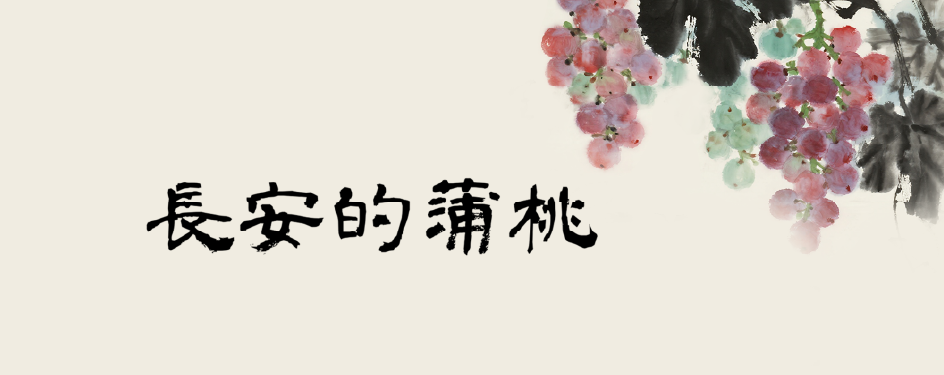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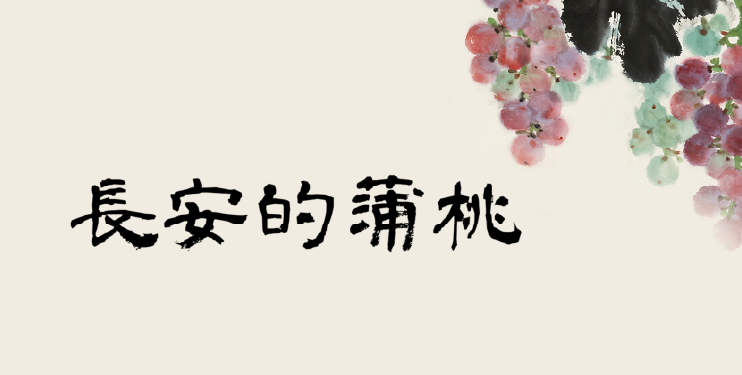
“強漢盛唐”,中國歷史上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兩個朝代,也是開疆拓土的時代。“萬國衣冠拜冕旒”的背後,卻是流離失所,戰火烽煙。詩人如何把眼前生靈塗炭的情景化為擲地有聲的詩句?
漢樂府素以質樸自然著稱,善用白描手法傳遞真摯動人的情感。“戰城南,死郭北,野死不葬烏可食。”《戰城南》首句直指戰爭的殘酷:陣亡的士兵無人收殮,逃不過被烏鴉啄食的悲慘命運。戰事頻仍的結果不只是屍橫遍野,更是對整個社會造成的破壞:“梁築室,何以南?何以北?禾黍不穫君何食?願為忠臣安可得?”橋上建造防禦工事,南北無法往來,道路不通,莊稼無人收割。食不果腹,要為國盡忠又談何容易。
殘酷的不單是戰事本身,還有因為長期征戍引致骨肉分離,老無所依。描寫老兵退役歸家的《十五從軍征》,讀來令人心酸。老人家“十五從軍征,八十始得歸”,當兵六十餘年,歸來已是家破人亡。昔日居處松柏成蔭,墳冢累累。“兔從狗竇入,雉從梁上飛”,庭園荒蕪,杳無人煙,老兵煮好飯菜亦無人分享。“出門東向望,淚落沾我衣。”戎馬一生,只落得晚景淒涼。
自初唐滅東突厥到晚唐黃巢之亂,兩百多年大唐烽煙不斷。天寶年間爆發的安史之亂,更令金玉其外的大唐露出其中敗絮。王昌齡《塞下曲》的“黃塵足今古,白骨亂蓬蒿”,杜甫《兵車行》的“君不見,青海頭,古來白骨無人收”,都直指亂世中人命如草芥。暴於荒野的白骨,一去不返的征夫,都是戰事連年的鐵證。
杜甫另一首名作《垂老別》寫於安史之亂,以正要踏上征途的老翁之口,道出戰爭如何慘烈。“積屍草木腥,流血川原丹”,草木散發屍臭,平原山川被鮮血染紅,觸目驚心。白居易《新豐折臂翁》的主人翁用大石捶斷手臂,以自殘避過遠征南詔,“一肢雖廢一身全”,算是如願以償,但舊患纏身數十載,每逢風雨陰寒,便痛得無法成眠。他卻說:“痛不眠,終不悔,且喜老身今獨在。”這種喜是何等悲酸諷刺。
唐代詩人喜歡以漢朝比擬本朝,原因有二:一是大唐之前只有大漢能與之媲美。二是要批評當朝國事,只能委婉其詞,借古諷今。反對長年征戰、同情戍兵征夫的詩人,自然把漢朝的人物和典故寫進詩中,以漢代唐,發出不平之鳴。
“誓掃匈奴不顧身,五千貂錦喪胡塵”出自陳陶的《隴西行》。匈奴與漢朝交戰百餘年,到唐朝時已與中原民族融合,史冊再無“匈奴”之名。奮不顧身的漢家兵將,其實是大唐男兒。杜甫《兵車行》“邊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開邊意未已”一句,謂漢武帝出兵開拓邊疆,大批士卒陣亡,仍無止息之意,其實是批評唐玄宗好大喜功,為開邊而頻繁徵兵。
李頎的《古從軍行》同樣以漢家借代李唐,不同之處在於加入意味深長的典故。“聞道玉門猶被遮,應將性命逐輕車。年年戰骨埋荒外,空見蒲桃入漢家。”這段歷史與汗血寶馬引發的戰爭有關。漢軍西征大宛,因斷糧而無法攻克,將軍上書請准罷兵。漢武帝龍顏震怒,遣派使者擋住玉門關,不准撤退。士卒後無退路,只能繼續作戰。雖然漢宛之戰以大宛投降告終,但天下虛耗,數萬兵卒葬身異鄉,對大漢並無實益,只是讓長安的皇親貴胄能啖嘗西域的葡萄罷了。
詩人把征夫戍卒的血淚凝煉成詩,讓我們在千百年後仍能看到硝煙不絕的戰場,聽見黎民百姓的悲歌,更加明白和平可貴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