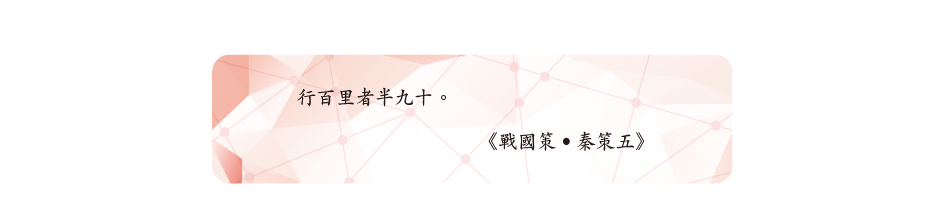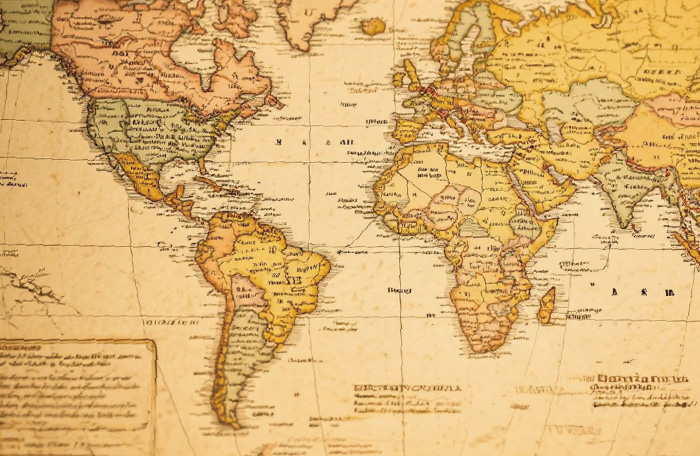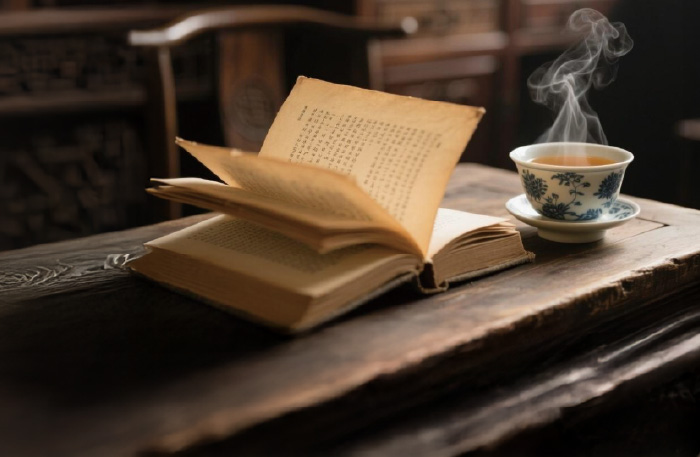“一姐不如二姐嬌,三寸金蓮四寸腰,輕搽五六七錢粉,妝成八九十分俏。”這首打油詩據說為才子倫文敘所作,充滿民間趣味。以數字入詩絕非打油詩的專利。騷人墨客興之所至,也會用平平無奇的數字寫景抒情,留下傳誦千古之作。
李白自言“一生好入名山遊”,初訪廬山,即景成詠,作《望廬山瀑布》,當中名句“飛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銀河落九天”,極言瀑布有三千尺高,雄奇壯麗,仿似從天而降。另一詩作《宣城見杜鵑花》曰:“蜀國曾聞子規鳥,宣城還見杜鵑花。一叫一回腸一斷,三春三月憶三巴。”太白暮年旅居宣城,見杜鵑花開,想起傳說中蜀帝死後化成杜鵑鳥,子規啼血,鄉愁油然而生。詩中的“一”和“三”字各自重複兩次,有如哀鳴不絕,纏綿悱惻。杜甫不讓詩仙專美,《絕句》每句嵌入一個數字:“兩個黃鸝鳴翠柳,一行白鷺上青天。窗含西嶺千秋雪,門泊東吳萬里船。”詩中妙用“一”、“兩”、“千”、“萬”四個數字,描寫鸝鳴柳間、白鷺在天、西山映雪、門泊舳轤的景致,有動有靜,聲色並茂。
宋人邵雍精研易經象數,對數字特別敏感,其《山村詠懷》饒富妙趣:“一去二三里,煙村四五家。亭臺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除數詞外,全詩只有十字,便足以勾勒出山村野趣。吳承恩《西遊記》第三十六回的數詩則字數較多,畫面亦更豐富。詩中倒序嵌入十至一之數:“十里長亭無客走,九重天上現星辰。八河船隻皆收港,七千州縣盡關門。六宮五府回官宰,四海三江罷釣綸。兩座樓頭鐘鼓響,一輪明月滿乾坤。”這首數詩雖然無關情節,但奇巧中不失氣韻靈動,果然是高手之作。
清人鄭板橋的《詠雪》亦是傳誦極廣的數詩。相傳鄭板橋到揚州訪友,途中遇上數名書生對雪吟詩。諸生見他一身麻衣粗布,便出言不遜。鄭板橋順口吟道︰“一片兩片三四片,五六七八九十片。千片萬片無數片,飛入梅花都不見。”詩人賞雪,一片一片數算雪花,由一到十,以至數之不盡,隨後詩鋒一轉,將雪花幻化成梅花。全詩不着一“雪”字,盡得風流,言雖簡而意無窮。諸生聽罷,嘖嘖稱奇,方知人不可以貌相。
文學與算術看似風馬牛不相及,卻有詩人數字邏輯特別強,作品包含加減運算。例如白居易有《自誨》詩,其中“人生百歲七十稀,設使與汝七十期。汝今年已四十四,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,疾速倏忽如一寐”數句,自忖行年四十四,設想壽數七十,屈指算來,驚覺人生只剩二十六個寒暑。光陰似箭,人生若夢,詩人感悟到自己更應樂天曠達,悠然自適。
更有趣的是,有人別出心裁,以算術入詩,寓數理於詩文。清代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收錄了不少數謎詩,當中以《以碗知僧歌》最為家喻戶曉。詩云:“巍巍古寺在山中,不知寺內幾多僧?三百六十四隻碗,恰合用盡不差爭,三人共餐一碗飯,四人共嘗一碗羹,請問高明能算者,算來寺內幾多僧?”寺僧用餐,僧多碗少,只好三人一碗飯,四人一碗羹,剛好用盡三百六十四隻碗,寺僧有多少人?若用代數方程式計算,應可輕易解謎,讀者不妨一試(答案見頁底)。數謎詩將刻板枯燥的數學運算,變成開動腦筋的謎語題,也可算是寓教於樂了。
數字看似是平淡不過的書寫符號,但在匠心之下,可以淬鍊成飛瀑千尺、雪花萬片,甚或待解之謎,讓人馳騁其中,感受無盡詩意與韻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