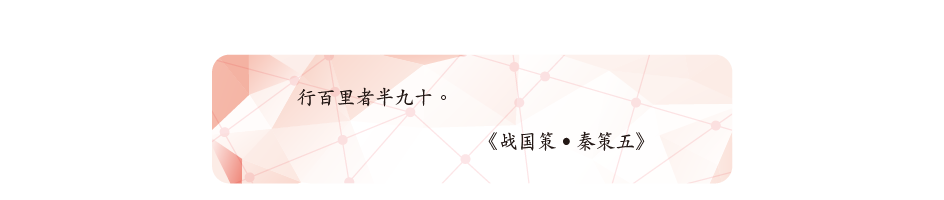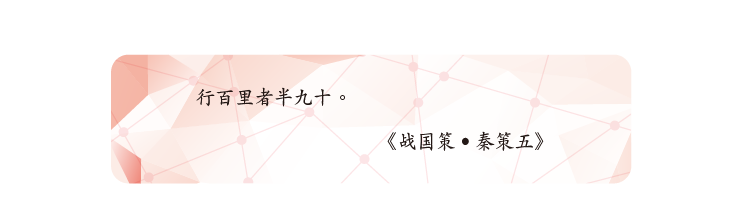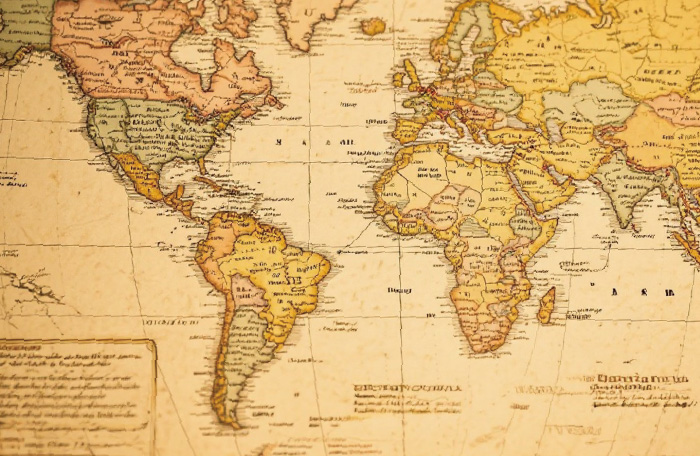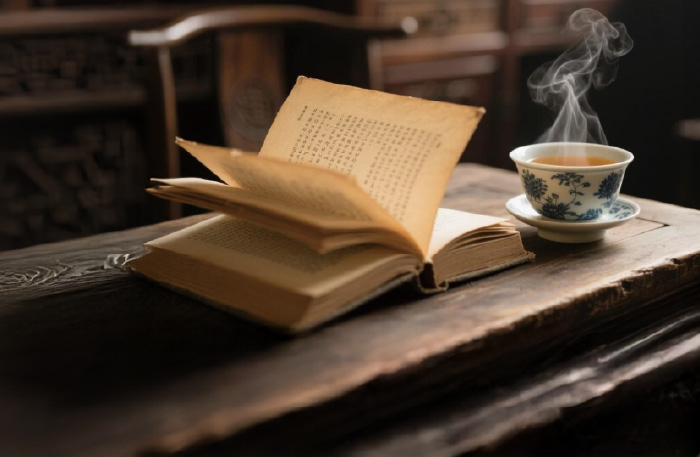“一姐不如二姐娇,三寸金莲四寸腰,轻搽五六七钱粉,妆成八九十分俏。”这首打油诗据说为才子伦文叙所作,充满民间趣味。以数字入诗绝非打油诗的专利。骚人墨客兴之所至,也会用平平无奇的数字写景抒情,留下传诵千古之作。
李白自言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初访庐山,即景成咏,作《望庐山瀑布》,当中名句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,极言瀑布有三千尺高,雄奇壮丽,仿似从天而降。另一诗作《宣城见杜鹃花》曰: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太白暮年旅居宣城,见杜鹃花开,想起传说中蜀帝死后化成杜鹃鸟,子规啼血,乡愁油然而生。诗中的“一”和“三”字各自重复两次,有如哀鸣不绝,缠绵悱恻。杜甫不让诗仙专美,《绝句》每句嵌入一个数字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诗中妙用“一”、“两”、“千”、“万”四个数字,描写鹂鸣柳间、白鹭在天、西山映雪、门泊舳轳的景致,有动有静,声色并茂。
宋人邵雍精研易经象数,对数字特别敏感,其《山村咏怀》饶富妙趣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除数词外,全诗只有十字,便足以勾勒出山村野趣。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六回的数诗则字数较多,画面亦更丰富。诗中倒序嵌入十至一之数:“十里长亭无客走,九重天上现星辰。八河船只皆收港,七千州县尽关门。六宫五府回官宰,四海三江罢钓纶。两座楼头钟鼓响,一轮明月满乾坤。”这首数诗虽然无关情节,但奇巧中不失气韵灵动,果然是高手之作。
清人郑板桥的《咏雪》亦是传诵极广的数诗。相传郑板桥到扬州访友,途中遇上数名书生对雪吟诗。诸生见他一身麻衣粗布,便出言不逊。郑板桥顺口吟道︰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六七八九十片。千片万片无数片,飞入梅花都不见。”诗人赏雪,一片一片数算雪花,由一到十,以至数之不尽,随后诗锋一转,将雪花幻化成梅花。全诗不着一“雪”字,尽得风流,言虽简而意无穷。诸生听罢,啧啧称奇,方知人不可以貌相。
文学与算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却有诗人数字逻辑特别强,作品包含加减运算。例如白居易有《自诲》诗,其中“人生百岁七十稀,设使与汝七十期。汝今年已四十四,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来事,疾速倏忽如一寐”数句,自忖行年四十四,设想寿数七十,屈指算来,惊觉人生只剩二十六个寒暑。光阴似箭,人生若梦,诗人感悟到自己更应乐天旷达,悠然自适。
更有趣的是,有人别出心裁,以算术入诗,寓数理于诗文。清代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收录了不少数谜诗,当中以《以碗知僧歌》最为家喻户晓。诗云:“巍巍古寺在山中,不知寺内几多僧?三百六十四只碗,恰合用尽不差争,三人共餐一碗饭,四人共尝一碗羹,请问高明能算者,算来寺内几多僧?”寺僧用餐,僧多碗少,只好三人一碗饭,四人一碗羹,刚好用尽三百六十四只碗,寺僧有多少人?若用代数方程式计算,应可轻易解谜,读者不妨一试(答案见页底)。数谜诗将刻板枯燥的数学运算,变成开动脑筋的谜语题,也可算是寓教于乐了。
数字看似是平淡不过的书写符号,但在匠心之下,可以淬炼成飞瀑千尺、雪花万片,甚或待解之谜,让人驰骋其中,感受无尽诗意与韵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