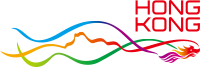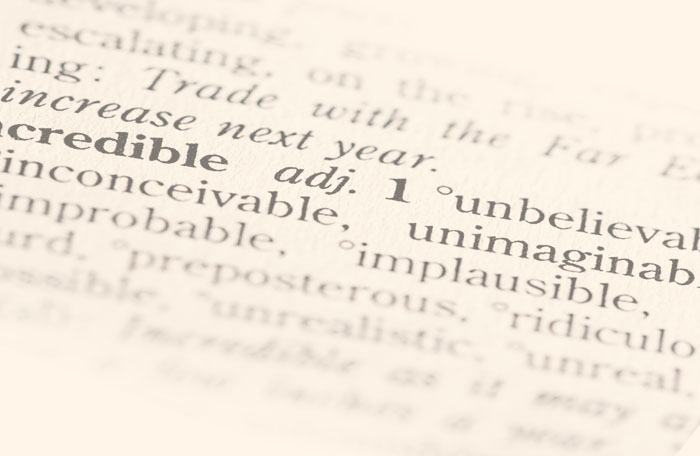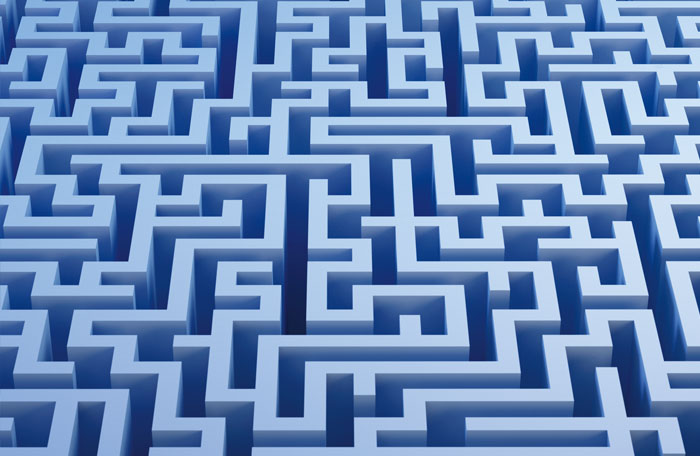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四十二分,中國唐山市發生7.8 級大地震,逾二十萬人死亡,十多萬人重傷,整個城市毀於一旦。
數十年過去了,唐山市的廢墟上重建起一座新城市,人們生活看似回到正軌,但破碎的心靈能夠完全修補嗎?二零零六年,正值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,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創作小說《餘震》。書中描寫一個母親在地震後作出艱難的選擇,以及這個抉擇如何影響一個七歲小女孩的人生,藉此探究災難對倖存者造成的永久傷害。這部作品獲推許為“至今寫地震寫得最好的小說”,二零一零年由內地導演馮小剛改編成電影《唐山大地震》。
小登七歲,既是父母的貼心小棉襖,也是雙胞胎弟弟小達的保護神。她活潑、快樂、倔強,但突如其來的地震改變了一切。姊弟倆在睡夢中,被壓在一塊水泥板下的兩頭,無論抬起哪一邊,都必定犧牲另一個。
小登聽見小舅厲聲喝斥着母親:“姐你再不說話,兩個都沒了。”在似乎無限冗長的沉默之後,母親終於開了口……母親石破天驚的那句話是:小……達。
這兩個字像重錘一樣,砸在女孩的頭頂。如果就此死去,她永遠是那個不識愁滋味的小女孩。可是,她竟奇跡似地活了過來。她搖搖晃晃地站起來,邁着蹣跚的腳步,決絕地走向未知的前方,離開了那個讓她心碎的家。其後,她被人領養,改名爲小燈。從這時起,小說和電影裏的女主角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《餘震》裏的小燈,心裏總有一扇鋪滿灰塵、緊緊關閉的窗戶。她不是電影裏那個與養父父女情深、與女兒相處融洽、與外籍丈夫婚姻美滿的方登;她是與養父恩斷義絕、與女兒水火不容、與丈夫感情破裂的小燈。她長年焦慮失眠,曾三度自殺未遂,須接受心理治療;她不是浴火重生的鳳凰,而是在苦海中掙扎求生的凡人。
小說結尾,小燈回到老家唐山,看到與她一街之隔的母親。母親已經當了奶奶,身邊還有兩個叫紀登和念登的孩子。她聽見母親罵:“紀登你個丫頭,忒霸道了些。”三十年前的記憶剎那浮現眼前,她彷彿就是那個未諳世事、無憂無慮的小丫頭。這時候,她聽見母親問:“閨女,你找誰?”終於,小燈流下了地震後第一滴眼淚,心中幽閉的那扇窗,也登時給推開了。
張翎本是聽力康復治療師。在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,她接觸過不少軍人、災民和難民,自稱“對疼痛的感覺絕不陌生,也不願意接受一切都會過去的膚淺安慰”。她希望通過對疼痛淋漓盡致的描寫,引起人們對災後心理創傷的關注。地震中被壓在水泥板下,是小燈一生痛楚的開始。當身體的疼痛過去了,心靈的悲痛卻慢慢沉澱,恍如隨時決堤的暗流。被生母捨棄、養母病逝、遭養父侵犯,這些經歷都令小燈缺乏安全感。她試圖牢牢地掌控身邊一切,卻沒想到抓得愈緊,失去得愈多。心靈痛苦,身體會有忠實反應。小燈患有嚴重頭痛,書中把她頭痛發作時的感覺描寫得非常形象化:
是一把重磅的榔頭在砸──是建築工人或者鐵匠使用的那種長柄方臉的大榔頭。不是直接砸下來的,而是墊了好幾層被褥之後的那種砸法。所以疼也不是尖銳的小面積的刺疼,卻是一種擴散了的、沉悶的、帶着巨大回聲的鈍疼。彷彿她的腦殼是一隻鬆軟的質地低劣的皮球,每一錘砸下去,很久才能反彈回來。砸下來時是一重疼,反彈回去時是另外一重疼。所以她的疼是雙重的。
張翎說:“儘管疼痛和醜陋都讓人不安,可是書寫《餘震》的目的並不是悅人耳目。”然而,小說所強調的“疼痛”,在電影裏由溫情取代。方登雖然被生母放棄,但成長期間並不缺乏愛。養父母待她如珠如寶,雖然大學時遇人不淑,但後來嫁給了對她千依百順的外籍丈夫,更育有一個很懂事的女兒。在汶川地震中,她看到了另一個母親的抉擇,瞬間明白了自己母親當年的絕望與悲慟,終於選擇與弟弟相認,回家見母親。當她看見媽媽年復一年為她買下的一册册課本,不禁放聲大哭,為自己數十年不通音訊向母親懺悔。電影就在方登一句句泣不成聲的“對不起”中進入尾聲。
小說《餘震》和電影《唐山大地震》,同是刻劃人被天災推到極限時的反應。小說側重自我救贖,尋求心理輔導,面對痛楚,走出陰霾;電影則強調親情能撫平心靈創傷。正如書中所說:“天災過去之後,每一個人站起來的方式,卻是千姿百態的。”無論如何,唯有走出心中樊籠,選擇原諒與寬恕,才能平息心中的餘震。